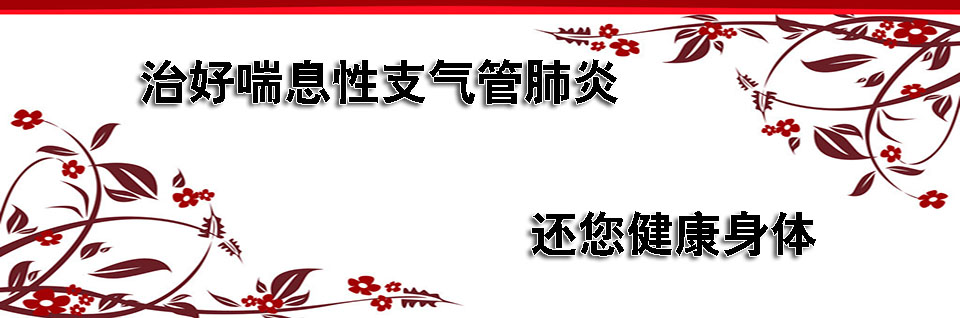当前位置:喘息性支气管肺炎 > 喘息性支气管肺炎检查 > 徽州水患 >
徽州水患
年7月初,歙县因灾情更改高考时间登上新闻头条后,年7月初,时隔1年,徽州又入汛期。
对此,你是否有这样的疑惑:徽州水患是近年新出现的问题,还是古来有之。如果是近年出现的,其原因是什么?
如果古来有之,面对水患,徽州人是如何应对的?本文不再陈述季风、副高对徽州的影响这种常识(因为我没找到动图,自己做太费事),仅以《明清徽州灾害社会与应对》(作者:吴媛媛)为基础材料,补入资料解答。
本文所有“()”内是我的见解,与原作者无关
当代的我们探讨明清时期,一小片区域的历史会否不准确?
我是徽州人,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由《明清徽州灾害社会与应对》的序章解答:
徽州区域狭小,明清正史、实录与清代档案中关于徽州的资料并不多,纵然有相关记载,大多也只是只言片语,所以这类材料,只能当做“辅助参考资料”。但是,徽州作为“东南邹鲁”,明清“文书”数量庞大,包含地方志、文集、日记、年谱、笔记小说、契约文书、村落文书、碑刻、宗族谱牒,且这些“文书”因徽州人整体文化素养高,其可性度也大于其他区域(个人认为还有数字教育普及、注重契约的社会氛围{不包含仆姓}这两方面原因,也提高了这些"文书”的可性度)。因此,我们对于明清徽州的探讨与研究,是可行的(忍不住“凡尔赛”一段,徽州虽也有“假文书”,譬如民国以后,仆姓、小姓造假族谱,但因为这些谱没办法与明清遗存对上,所以其危害尚不足以达到否定徽州所有“文书”的程度)。
徽州的水灾严重吗?
《明清徽州灾害社会与应对》给灾害定级做了详细的图表,我在此做简略概括:
同赤地千里的北方大旱、千里无人烟的黄河流域大水灾想比,徽州是“山水清冽,素无大灾”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徽州没有因“水”受灾(初步了解徽州戳我),嘉靖《徽州府志》中,有这样的描述:“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潴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意为,徽州因地形原因,备受旱涝之苦)。
这是龙川
龙川胡氏宗祠,注意台阶高度
昨天宣城公安发布的龙川图(龙川胡氏宗祠仪门拍摄)
昨天宣城公安发布的龙川图(龙川胡氏宗祠仪门拍摄)
(下面两张图虽然很美,但是想象一下,暴雨过后,山间溪水向低处汇聚,进入穿村河流。图一尚算作“平地”较多的区域,图三......)
我是图一:绩溪家朋
休宁
我是图三
(所以在村落选址营造或扩建的时,会出现这样的村落)
玉带缠腰,水流冲击后,村庄的土地会越来越多
迎水冲击面是不会有古村的,有的话一定是新建的
(说完地形,再说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暴雨猝不及防+防也防不住,大禹治水靠疏。我不是专家,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今年涨水频率越来越高,不能总归结于“地形、气候决定了徽州很容易涨洪水,即便整个夏季的平均降水量不高,也不会对涨不涨水造成大的影响”吧)。
徽州人如何应对水患?
(除了村落扩建或初建时,注重地理方位外,徽州古村还有着自己的动力水系)。
(“动力水系”如何运作,说过很多次,再此不赘述,简略概括:枯水期引水入村;丰水期闭闸,任水流绕村而去;下水道中可赶牛用以清淤。
纵然如此,西溪南依旧不能说是未遭遇过水患的村落,只是相对而言,受灾频率、受灾程度有多环节)。
洪武元年至民国十二年,年间,徽州府一府六县各自独立计算,总计发生水患次(注意,是各自独立的总计,假若同一时间段,绩溪、婺源都发生了水灾,便会被记为2次)。
(像近年这样,连续水灾,是很难从明清数据中佐证其合理性的,虽然也有过这种情况,但不是常态。我只能猜测,这是因为明清乃至民国年间,资讯流通度差,无法将所有数据收集齐;亦或是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我们进入了易受旱涝灾害阶段。我个人更认同后面这个猜测,但作为非专业人士,不能通过看几篇文就下结论,这结论应当由专家下,我们只能猜测)。
《明清徽州灾害社会与应对》中关于水灾对于农作物的影响等,在此亦不赘述(我已经在《流动的故乡》中提及,水稻种植对徽州的重要性以及佛教在徽州传播与祈雨密切相关这两点)。
接下来,我们看看徽州的赈灾程序
书中将赈灾分为如下几步,并附上具体案例:
本地士绅们着手查赈、劝募赈灾款项(地方士绅第一时间组织赈灾);
地方政府需要在接到上级的命令后,才会前往勘查灾情,譬如宣统年间,休宁发生水灾,士绅们都已经自发性的完成了第一批急赈任务,知府刘汝骥才接到两江总督的命令,不得不前往休宁勘查灾情(此时已是灾情大约一个月后了)。
刘知府查灾情时,省级政府下令厘局(类似于税务局)拨款两赈灾,但银差相到位,灾民们又迫切需要钱,所以士绅们从厘局拨白银千两兑换成英洋.元,再由士绅补上余元,先行减半发给灾民。
随后,因为灾情广大,省级政府再下发湘平银(晚晴币制混乱,记账货币就有湘平银、库平银、制钱、外国银圆四种,又有京平与库平两种折算比例,无需细究此时的具体比例,只要知道这是发钱了即可)二千两,这笔费用是专门拿来抚恤死者的。
除了直接发钱,以工代赈也是赈灾手段之一。水灾一定会损毁路、桥这样的公共设施,雇佣受灾民众以及没有活计的穷民参与施工建设,一方面能避免灾民养成惰性和依赖性等弊病,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受灾区域早日回归正常秩序。
书本没有图片,我补一份我们收集的资料作为赈灾的补充,以下内容与推荐书目无关
义赈是旧时徽州最具广泛社会影响力和强大活动能力的民间赈灾机制。
清光绪十五年,屯溪茶商成立屯溪公济局,救助社会弱势群体,为“救助事业”提供民间专属部门。
清光绪三十四年,徽州爆发特大水灾。徽宁两府商人捐助赈灾,灾情缓解后,善款多出了三千两,依据近些年在上海目睹“同乡中之贫病无依者甚多”的情况,徽宁商人开会决定用这三千两建一间“徽宁医治所”为同乡谋福利。
宣统3年15间用于“寄宿医治”的平房完工,名字由最初构想时的“徽宁医治所”改为““徽宁医治寄宿所”,除了对极度困难的同乡进行免费救助、稍困难的老乡进行低价医疗救助外,这间寄宿所还为经商失败、无家可归的同乡提供廉价(特别困难者免费)寄宿服务。维持寄宿所营运的费用由徽宁两地商人捐助。
“徽宁医治寄宿所”虽是福利机构,但也有自己的“规矩”:因打架斗殴而受伤者、花柳病患者,绝不援助。
民国二十一年,屯溪再建“屯溪残废乞丐教养所”,教授残疾人、乞丐谋生技能。
摄于年6月屯溪残废乞丐教养所
我们在拍的相关资料
我们在拍的相关资料
我们在拍的相关资料
你可能会奇怪,我为什么没有在本文中提及宗族在赈灾过程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我觉得不用提,不能下结论,不想有无谓争吵,对此部分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找相关文章,选择自己支持的观点。
我们与游学徽州
游学徽州.8月13至8月16日:古村+古建+定制木构搭建、非遗体验
徽州虎患
不“传统”的汪满田鱼灯会
流动的故乡:徽州(一)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