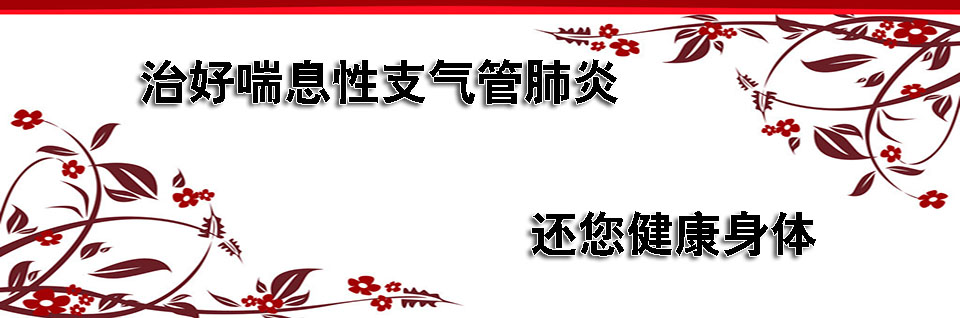当前位置:喘息性支气管肺炎 > 喘息性支气管肺炎治疗 > 县城可以混,但不适合这些人 >
县城可以混,但不适合这些人
昨天市井财经刊登了中国县城的规则一文,获得朋友们一致好评。今天这篇文章就讲讲:县城应该怎么混。
县城宜居小家而不宜创大业,宜独善其身而不宜兼善天下,宜养其气而不宜伸其志,宜庸常模式而不宜特立独行。
■文|酱香老范
■来源|不是官话(ID:bushiguanhua)
中国内地现有个县。县城作为一个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善之区),是城乡之间最主要的中介,可谓“城市之尾、农村之头”,或曰“准城市”。有网友说:“北上广是中国的幻象,县城才是中国的底色。”
邓丽君在《小城故事》中唱道:“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如写一篇《生活在小县城的N个理由》,我至少可列出一打说辞。如生态环境较好,工作和生活节奏不像城市里那么快,房价相对不是很高,通勤方便,人际间多少尚存人情味,因交际半径小彼此易牵线搭桥,到乡村去休闲度假便捷等。原本信息闭塞是小县城的通病,而今网络普及,这已不再算局限性。
上海作家周泽雄在《小县城的活法》一文中,引浙江某县城文友的话:“据可靠数据统计,中国人夫妻生活的质量,小县城里的居民位列第一,城市越大,排名越后。”他还说:“我稍一细想,觉得话虽糙了点,但也不无道理。谁让我们生活节奏这么快?生活压力这么大?看看他们,一顿饭可以吃上三个小时,单位与家庭的距离通常不会超过一公里,同事和邻居往往合二为一,随便在街上走走,都可能碰到十来个熟人,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可能遭遇到一份亲切。那份不把时间当回事的从容劲儿,看着也能闻出一股茶香,哪像我们,整天把日子当牲口赶。”《新周刊》年有一篇《最适合我们的生活状态,是在大城市过小县城的日子》。“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不算很离谱。
不过,县城人倘盲目乐观,少自知之明,一味自夸小县城“真不错”,则显失明智,且显得没见过世面。其实,都市人羡慕小县城里的生活,不过是出于“围城”心理。小县城纵有千好万好,但有一条就足以令其在大城市面前抬不起头来。那就是要大有作为,就得走出小县城,闯荡大都市。
吴昌硕倘一辈子在安吉老县城里的“芜园”耕读,而不到苏州、上海,恐怕只是一个小有才情,且很用功的乡村画师罢了。鲁迅倘不走出绍兴,何以鲁迅?沈从文20岁时离开小县城“凤凰”到京城,才成就其骄人业绩。钱理群被分配到贵州一山区小县城当语文老师,“文革”后考上北大研究生,后来成为名教授。余华以江南小县城的牙医身份开始写作,其成“正果”并不在小县城。贾平凹在《秦腔》中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在县上工作长了,思维就是小县城思维,再这样呆下去……只能是越来越小,越来越俗,难登大雅之堂!”有志青年岂可不慎乎?
“小县城思维”的特征,首先可概括为“自以为是和自以为不是”。“自以为是”指是在乡下人面前,自以为是城里人,见多识广,在县城里老吃老做,熟门熟路,自信多多。而“自以为不是”,指的是县城人知道自己不过是小小县城之人,真正到了大城市,又会缩头缩脑、蹑手蹑脚,自信顿失。这庶几近于鲁迅说的“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
这种人文背景,最适合“半桶水”的人。那些不上不下的家伙,在小县城大多混得如鱼得水。某县机关公务员下乡时,爱向乡村干部大谈“区块链”,而接待省厅来人时,则大讲乡村俚语俗谈。于是,基层的人以为他和国际新潮接轨,上头的人认为他对基层情况熟,且谈吐有趣,印象大好。
“大城市里有的,我们也尽量不要拉下”,是“小县城思维”的另一个特征。多年前,《北京青年报》女记者黎宛冰写某县城的一段话不乏代表性:“这个小城和中国的大多数小县城没有多少区别,唯一能标明它是座城市的是,一个街心的广场,广场上有一座矫揉造作的雕塑,这些僵硬的人手心向天,你争我夺地顶着一只球。
我在小城里总见到这样的雕塑,以各种形式顶个球:工农兵顶个球,民主和科学顶个球,人类和动物顶个球,虚构和现实顶个球,男人和女人顶个球,它们分布在许多城市里,变成标志城市文明的丑陋景观。”小县城固然要向大城市学习,但问题是大城市里的许多好东西,一旦到了小县城就会变味,变得不是滋味。恶俗本身倒还可以原谅,让人不大受得了的是把恶俗当高雅,视肉麻为有趣。
另一方面,文艺家们对小县城也多有不屑。小说、电影以写(拍)城市或农村为多,小县城常是被遗忘的角落乃至盲区(贾樟柯曾是例外)。韩浩月在《中国青年报》上有过《热闹的县城,落寞的县城文化》一文。难怪年轻人感叹:“北上广容不下肉身,小城市放不下灵魂。”
“官本位”意识特浓是“小县城思维”又一个显著特征。网上有一篇署名白靖平的“深度好文”《混在县城》,作者发激愤之言:“在县城,只有官场,没有职场。”因为“一官半职在都市是职业,在县城就是领导”。小县城里虽无大官(撑死不过正处级),但“官本位”意识“浓得化不开”,这是“小县城思维”最可诟病之处。
孟庆德在《小县城》一文中写道:“小县城小,机关衙门的楼房和门脸也就小,但机关衙门里的人架子都很大,比省长还大。参加过一次宴会,十几张桌子都坐满了,人们等了许久,餐厅大门终于打开,一些科级的局长穿着讲究地被人簇拥进来,进来是进来了,都高抬着头,谁也不看,一径向专门为他们安排的单间走进去。”官场如此,民间同样不能免俗。
“混在县城”,最重要的是人脉关系和人情交往。有关系的顺风顺水,没关系的死蟹一只(谚曰“拎着猪头寻不着庙”,或“关系不接轨,烧香引出鬼”)。这既带来“熟人好办事”的便利,也导致私人空间的坍塌。在小县城,任何人的生活都很容易被别人掺上一脚。那些喜欢打探和传播别人私生活的人,其嘴脸长得像电视发射塔。
由现代文明所带来的规则意识、边界感和相对公平的机会,在大城市较多而小县城较少。已习惯城市生活规则的人,回到县城会有明显不适。另外,小县城文化消费普遍不高,想要找到多少“文化氛围”和“文化品位”,泰半是奢望。至于文化名人,比晨星更寥。年以陕西省长安县文科状元身份考入北大中文系的陆步轩,后来发配回原籍,在县城街头卖肉,一不小心成了“新闻人物”。
因盛行“官本位”,县一级不大重视人才(专才)。有的人在大城市混不好,以为回小县城会被当个宝,结果还是根草。而京城或省城什么人,只要头衔“高大上”,哪怕是鸟人,到了县里也会在场面上被供起来。我在县城听过某些不乏来头的专家、学者做报告,其对中国县情、乡情两眼一抹黑,所论牛皮哄哄,大而无当,一点不接地气,就像我那文盲外婆说的“书读到屁眼里去了”。
眼下各地搞城市化,用行政手段的擀面杖,摊大饼似地拉大城市镇框架。倘邓丽君再世,当唱“拆的拆,建的建,小城建设真是快”。不少县变成了县级市或大城市的一个区。县城真正原住户的比例如今已越来越低,而越来越多的是从乡村来此定居的各色人等。此大势不可抵挡,问题是广大县城原来就缺少现代公民社会意义上的“市民”,而新进住县城者,更不会随居住地的改变而自动变成“市民”。于是,小县城里既一以贯之地保留和传承了“城里人”的种种劣根性(类似鲁迅说的“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又平添了一种中国式农民特有的狡黠。不城不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似城实乡,颇有圆机活法。
上述种种并不是小县城不良文化之要害,私忖其致命伤在容易颓损人的精神,导致不思进取,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丧失自强不息、励精图治的心志。如生活在地方特产较丰、人均收入较高、生态环境较佳、社会治安较好、民风乡风较淳的山区、半山区县的县城,更易如此。小县城的人要走向大舞台,除了要有更多的奋斗精神,还要有对失去过往安逸生活之想念的强大免疫力,否则,虽出而又泯然众人矣。
以笔者积半个世纪小县城生活之体验,感受如下:小县城宜居小家而不宜创大业,宜独善其身而不宜兼善天下,宜养其气而不宜伸其志,宜庸常模式而不宜特立独行,宜“万金油”而不宜术有专攻,宜花小钱而不宜挣大钱,宜洗头足浴、桑拿按摩、品茶喝酒而不宜读先锋诗歌、观实验戏剧、看独立电影,宜打牌钓鱼而不宜读硕读博,宜听地方戏而不宜赏交响乐,宜得花柳病而不宜得抑郁症,宜友朋而不宜同志,宜结婚而不宜离婚……好在笔者素无大志,更无宏才,年复一年在小县城里苟且,就像在围棋盘上“二路”爬活……
本文为作者独立观点,且不构成投资建议。市井财经授权发表。
--全文完--
国庆聚惠立享全店购物88折
点击图片领取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