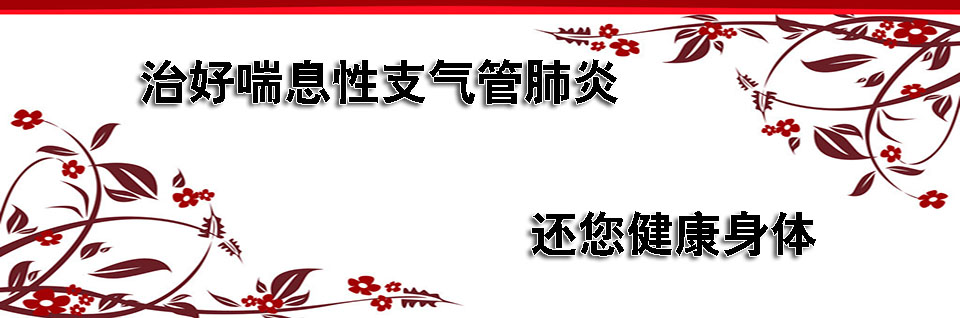当前位置:喘息性支气管肺炎 > 喘息性支气管肺炎饮食 > 病毒性肺炎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和对应的细胞 >
病毒性肺炎不同阶段的病理变化和对应的细胞
2021治疗白癜风最好的药 http://pf.39.net/bdfyy/bdfzg/140331/4365542.html呼吸道中的细胞不断暴露在外部环境中,使肺部成为特别容易感染的部位。呼吸道感染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疾病和经济负担。因此,预防和治疗呼吸道病毒相关疾病都是至关重要的。病毒的清除和感染的解决需要一个复杂的、多方面的反应,由常驻呼吸道细胞和先天免疫细胞发起,最终由适应性免疫细胞解决。虽然消除病毒病原体的有效免疫反应是必不可少的,但长期或夸大的反应可能会损害呼吸道。免疫介导的肺损伤在临床上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取决于损伤的位置和程度。因此,抗病毒免疫反应代表了清除病毒和免疫介导的肺损伤之间的平衡行为。1,人类具有大同小异的生理和病理大咖专家和一般专业人士,还有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人体具有一定的自愈能力。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面对病毒引起的重症肺炎,没有特效药物治疗,只能医学介入对症支持治疗。那么,为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人群后出现的后果不一样?有些人无症状,有些人轻微流感样症状,有些人则像SASR那时一样出现重症肺炎甚至死亡。这就是不同人群的人体具有不同程度的免疫力,而且负责机体组织细胞更新换代的干细胞的功能有差异。
2,呼吸道病毒严重威胁人类的身体健康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流感病毒感染和相关并发症是导致死亡的十大原因之一,平均每年有20多万人住院,估计有人死于与季节性流感病毒感染有关的呼吸道和循环并发症[1]。其他呼吸道病毒,如高致病性禽流感、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一直是人类健康的威胁。SARS-CoV在-年流行期间发生了变异,以更好地与其细胞受体结合,并优化在人类细胞中的复制,从而增强毒力[2]。相比之下,自被发现以来,MERS-CoV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异来增强人类的传染性[3]。但是-nCoV的致病性可能低于MERS-CoV和SARS-CoV[4]。有专家提出,我们对呼吸道病毒传播性和致病性之间关系的许多思考都受到了我们对甲型流感病毒的理解的影响:禽流感病毒在人与人之间有效传播所必需的受体特异性的变化导致了趋向性从下呼吸道转移到上呼吸道,从而降低了疾病负担[4]。比如,大流行性H1N1病毒-与上呼吸道受体结合-导致相对轻微的疾病,并在人群中成为地方性流行病,而H7N9病毒-与下呼吸道受体结合-有大约40%的病死率,到目前为止只导致了几个人传人的小范围[4]。3,病毒性肺炎的病理生理变化
正常的呼吸功能依赖于肺结构的保护以及气道和循环之间的内皮-上皮屏障。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引起的气道上皮细胞脱屑或流感感染期间气道上皮细胞增生-导致更严重的呼吸功能损害。上皮性粘液分泌增强、血管渗漏、水肿、粘膜炎症和上皮性塌陷。炎症细胞对感染的上皮和组织驻留的先天免疫细胞信号的反应而涌入,会增加水肿、血管充血和组织肿胀,进一步限制通过较小气道的气道[5]。细支气管末端是气体交换的场所,构成了肺的大部分气道表面。和RSV和肠道病毒D68等病毒相比,流感病毒和SARS-CoV和MERS-CoV冠状病毒更频繁地到达细支气管,因此更有可能扰乱肺功能并导致肺炎[6]。在感染期间,紧密连接的丢失、血管渗漏、肺泡腔内水肿液体和纤维蛋白的积聚可导致肺泡细胞坏死和透明膜形成。严重的原发性病毒性肺炎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7,8]。临床上,ARDS的急性期的特点是紫癜、低氧血症、肺水肿和随时间增加的呼吸衰竭,导致多器官衰竭和高死亡率。ARDS急性期呼吸衰竭的主要原因是发生气体交换的肺泡上皮-内皮屏障受损,导致肺泡腔充斥着含有纤维蛋白、红细胞和炎性细胞的蛋白性水肿液体,减少了肺泡气体交换,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9]。4,直接病毒损伤
病毒必须复制和协调病毒粒子成分的组装,才能产生子代病毒并自我繁殖。这通常是以感染细胞为代价的。SARS-CoV和MERS-CoV倾向于感染肺内上皮细胞[10,11]。与SARS-CoV或MERS-CoV不同,-nCoV在原代人气道上皮细胞中生长得更好[3]。阻止病毒复制的一个根本但最终有效的反应是让受感染的细胞通过凋亡自毁,但是一些病毒已经进化出逃避这一点的策略[12]。细胞出现病理变化或死亡也可能是病毒侵占宿主细胞进行自我复制和代谢过程造成的[12]。因此,在感染过程中,病毒直接引起的感染细胞的死亡在肺部病理中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许多临床后遗症和呼吸道细胞损伤是宿主对病毒和病毒感染细胞反应的结果。感染后很早,甲型流感病毒通过直接抑制上皮性钠通道(ENaCs)而导致肺泡腔内液体积聚[13]。在感染的后期阶段,甲型流感病毒诱导的上皮细胞死亡是上皮-内皮屏障损伤的主要原因[14]。5,宿主的抗病毒反应
(1)感知病毒肺泡细胞是上皮-内皮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呼吸道上皮细胞最早被病毒感染后,模式识别受体(PRRs)在呼吸道上皮细胞中激活,对于限制病毒传播和提醒免疫系统对感染做出反应是至关重要的。病毒感染激活这些细胞中的模式识别受体,触发I型和III型干扰素(IFNs)和其他促炎介质(如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抗菌肽)的产生和释放,从而启动宿主的先天和获得性免疫反应。气管支气管上皮细胞作为甲型流感病毒(IAV)最早的感染靶点之一,是IAV最早感知的部位之一。当IAV基因组从vRNP转变为单链、双链和单链RNA中间体时,宿主细胞的感知是由RNA与宿主细胞模式识别受体(PRRs)结合而触发的,启动了直接抑制IAV复制的抗病毒信号通路,以及促进IAV感染细胞清除的先天和获得性免疫细胞的招募和激活[15]。虽然呼吸道上皮细胞是大多数呼吸道病毒的主要靶点,但病毒可以感染内皮细胞,内皮细胞是肺中最丰富的细胞类型。内皮细胞在呼吸道发病中的作用程度部分取决于病毒的亲和性,而且往往具有物种特异性。例如,人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效地感染肺血管内皮细胞,导致内皮细胞激活,但也导致细胞死亡[16]。相比之下,流感病毒一般不会感染人类内皮[17]。与大多数呼吸道病毒不同,汉坦病毒(hantavirus)主要针对微血管内皮细胞,导致严重的微血管渗漏和肺水肿;值得注意的是,以肺部充满液体为特征的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死亡率为38%[18]。(2)肺局部的抗病毒反应有意思的是,呼吸道上皮细胞分泌大量广谱抗菌/抗病毒产物,直接抑制呼吸道病原体,在某些情况下调节免疫反应。肺部中含量最丰富的抗菌因子是溶菌酶、乳铁蛋白和分泌性白细胞蛋白酶抑制剂(SLPI)、β-防御素[19,20]。乳铁蛋白是一种由粘膜上皮分泌的糖蛋白,通过直接结合病毒并阻断病毒进入细胞所使用的宿主受体,可以防止DNA和RNA病毒感染细胞[21]。溶菌酶和SLPI虽然对一些微生物病原体有效,但在肺部的抗病毒能力有限。然而,SLPI保护粘膜上皮细胞免受炎症细胞释放的蛋白水解酶的破坏,从而限制肺损伤和促进伤口愈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2]。呼吸道上皮细胞组成性地产生一氧化氮(NO),暴露在促炎细胞因子和呼吸道病毒中会进一步增加NO的产生[23]。NO及其活性产物抑制病毒蛋白、转录和复制[24]。但是NO不分青红皂白的活性还可以修饰宿主细胞蛋白,并诱导产生有毒的细胞物种,如自由基和活性氮中间体,从而损害肺上皮[24,25]。(3)即时的干扰素应答许多不同类型的细胞传感器可以检测病毒并诱导I型干扰素-α和干扰素-β的表达。I型干扰素也可以直接激活免疫细胞(如刺激吞噬、树突状细胞成熟),以及间接启动免疫反应(如刺激呼吸细胞产生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I型干扰素的内在抗病毒活性包括阻碍病毒进入细胞、复制、转录和翻译[26]。I型干扰素刺激干扰素-γ(II型干扰素)的产生和分泌,进而激活巨噬细胞和吞噬细胞,增强树突状细胞的抗原提呈,并直接限制病毒复制[27]。I型干扰素还可以增强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的细胞毒活性,从而促进病毒感染细胞的清除,防止病毒的进一步传播[27]。干扰素通过激活DC和T细胞间接促进体液免疫应答,但它们也可以直接激活B细胞,促进强健而有效的病毒特异性抗体应答[28]。与几乎在所有身体细胞中表达的干扰素受体不同,III型干扰素的产生主要局限于肺部的上皮细胞[29]。与I型IFN一样,III型IFN激活JAK/STAT信号通路,从而在气道上皮细胞中引起与上述I型IFN相似的抗病毒生物活性[30,31]。有趣的是,作为对病毒刺激的反应,人类气道上皮细胞产生的III型干扰素-λ比I型干扰素更多,因此,III型IFN可能比I型IFN更有效地对抗呼吸道细胞中的病毒感染[31,32]。IAV感染触发分泌干扰素-γ的细胞毒性T细胞的增殖和募集,这对IAV的最终清除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干扰素-γ同时抑制肺泡巨噬细胞的细菌吞噬,很可能是通过抑制细胞表面肺泡巨噬细胞的清道夫受体[33]。(4)病毒感染的早期免疫反应(4.1)肺中性粒细胞:抗击病毒的第一线卫士肺中性粒细胞是第一个动员起来对抗病毒感染的先天免疫细胞亚群,在流感病毒感染后1天内到达肺泡,对感染的病毒进行吞噬清除[34,35]。它通过ROS的产生、吞噬以及蛋白酶和其他水解酶的释放来介导更广泛的抗病毒活性[36]。肺中性粒细胞持续增多到感染后第7天,高峰出现在感染后3-5天[37]。在小鼠中,较高的中性粒细胞数量与病毒诱导的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一致相关[34,35,37-39]。中性粒细胞在清除感染细胞和清除微生物病原体、死亡细胞和碎片方面表现出色。呼吸道病毒一般不会感染中性粒细胞,但会吞噬含有病毒的病毒粒子、病毒颗粒和凋亡小体[40]。一旦吞噬病原体,中性粒细胞利用细胞内颗粒和NAPDH氧化酶产生的活性氧释放的大量蛋白水解酶和抗菌肽来杀死或灭活病原体[41]。中性粒细胞还分泌的一些抗菌肽包括防御素、乳铁蛋白、溶菌酶和抗菌肽LL-37[42]。充足的中性粒细胞招募和活性控制病毒传播,减轻严重疾病。然而,过度的中性粒细胞反应会导致不受控制的炎症和对呼吸道上皮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损害,从而对宿主有害[40,43]。释放到细胞外间隙的ROS、水解酶和髓过氧化物酶可以损伤肺泡上皮和内皮,从而破坏上皮-内皮屏障[9,44]。正常情况下,中性粒细胞这种非特异性的、有效的吞噬作用和细胞毒活性通常是短暂的,然后由巨噬细胞清除凋亡中性粒细胞留下的凋亡小体和碎片。如果中性粒细胞的程序性细胞死亡或巨噬细胞的清除受到损害,呼吸系统和免疫细胞都可能暴露在传播严重炎症和急性肺损伤的破坏或激活因子中[45]。中性粒细胞可能通过分泌干扰素-γ或抗原提呈来促进T细胞反应和支持B细胞的活性[41,46]。肺单核细胞在感染后第2天开始募集,在感染后第5天达到高峰[38,47]。这些肺单核细胞的一个亚群也分化为一种髓系细胞,在感染后7-10天达到高峰[47-49]。CCR2依赖的这种髓系DC在感染后第7天促进抗IAV细胞毒性T细胞在肺部聚集,并可能反映了对细胞毒性T细胞清除IAV的依赖[49]。炎性单核细胞具有强大的抗病毒活性,对控制感染和减轻疾病严重程度至关重要,构成了肺泡巨噬细胞分泌的I型干扰素介导的抗RSV病毒活性的一个重要机制(I型干扰素募集炎性单核细胞)[50]。(4.2)肺泡巨噬细胞:自始至终的抗病毒积极分子肺部的巨噬细胞,即肺泡巨噬细胞,位于肺泡上皮的管腔表面,从而不断地遇到从外部环境吸入的颗粒和外来抗原[51]。肺泡巨噬细胞被认为是组织保护性的,因为肺泡巨噬细胞的耗竭与肺炎链球菌感染后损害组织的肺中性粒细胞的有害积累[52]、A型流感病毒感染后的疾病发病率增加[53]以及肺变应原致敏后促炎细胞因子的产生增加[54]有关。肺泡巨噬细胞介导的保护作用很可能是通过抗炎和免疫抑制机制的相互联系来介导的,因为肺泡巨噬细胞还可以通过肺泡巨噬细胞-上皮缝隙连接相互传递免疫抑制信号[51],并通过其组成部件产生TGF-β和维甲酸来诱导调节性T细胞(Treg)的发育[55]。呼吸道病毒感染后,肺泡囊环境迅速改变,加上对病毒抗原的感知和对促炎介质的暴露,使肺泡巨噬细胞具有促炎表型,这有助于启动宿主免疫反应和病毒清除[56]。虽然保护机制尚不清楚,但肺泡巨噬细胞在呼吸道病毒感染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在RSV感染期间,它们负责早期细胞因子和干扰素的产生,从而协调最初的抗病毒反应[50]。激活的巨噬细胞表达共刺激分子CD86,它促进FOXP3+调节性T细胞(Treg)的扩张,以抑制中性粒细胞驱动的细胞因子释放[57]。突显这些细胞的重要性的是,将Tregs过继转移到免疫缺陷小鼠中,控制了IAV感染期间免疫介导的致命性炎症[58]。(5)病毒感染的中晚期免疫反应如果病毒数量少,肺部的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则能顺利清除感染的病毒,感染者就感觉不到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不能被顺利清除而进入高复制增殖阶段,则身体动用其他的免疫细胞来支援以持续抗病毒。(5.1)NK细胞:直接杀伤NK细胞在几天内对病毒感染作出反应,释放细胞毒颗粒,产生大量干扰素-γ,或利用抗体依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抗体结合感染细胞表面表达的病毒蛋白以杀死病毒感染的细胞[59,60]。NK细胞能够区分正常细胞(通过抑制性受体)和病毒感染或转化的细胞(通过激活受体)。激活受体可以识别病毒或肿瘤抗原,进而清除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在中性粒细胞招募之后,但在效应T细胞到达之前,NK细胞还通过产生干扰素-γ来增强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的活性[59,61,62]。然而,一些流感病毒株,已经进化出伪装抑制性受体信号的机制,防止了NK介导的杀伤[59]。甚至一些呼吸道病毒感染NK细胞可以诱导凋亡,限制NK细胞的数量,因此,早期的细胞毒作用可以控制病毒的传播[40]。肺NK细胞的耗尽不利于病毒清除,从而导致更严重的疾病[59,61]。总体而言,NK细胞似乎主要通过清除病毒、促进CTL反应,在呼吸道病毒感染期间发挥有益的作用。(5.2)DC细胞:识别和提呈病毒抗原树突状细胞(DC细胞)可由病毒通过PRRs直接激活,也可由呼吸道上皮和其他肺部免疫细胞释放的促炎趋化因子和细胞因子间接激活[63]。在肺部,DC主要与呼吸道的粘膜上皮细胞相关,作为APC发挥作用,通过抗原提呈激活CD8和CD4T细胞的增殖和分化[63,64]。CD+DC在感染后2-4天内迁移到引流淋巴结,在那里它们有效地激活了识别病毒抗原的CD4和CD8幼稚和记忆T细胞,来控制呼吸道病毒感染[65,66]。CD11b+DC到达引流淋巴结的时间稍晚(感染后5-7天),在那里它们可能促进先前激活的效应CD8T细胞的扩张,并分泌大量的促炎趋化因子[63,64]。在实验性病毒感染中,阻断DC活性或CCR2缺陷可提高存活率并减轻严重的肺部病理,而DC的完全耗尽会导致病毒传播失控和更严重的疾病[63,67]。(5.3)体液免疫应答:B细胞和CD4辅助T细胞B细胞主要通过产生病毒特异性抗体来清除病毒,这些抗体可以(1)中和、调理和灭活病毒粒子或(2)启动对受感染细胞的杀伤。防止传染性病毒粒子从受感染的细胞扩散到邻近的细胞是控制病毒传播的关键。B细胞产生的中和抗体通过阻断病毒表面与宿主受体结合的蛋白进入细胞,有效地阻止了游离病毒粒子入侵未感染的细胞。抗体可以与感染细胞表面表达的病毒蛋白结合,触发补体级联和抗体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最终消除感染细胞的过程。当B细胞缺乏时,CD4T细胞不再足以起到保护作用,在感染SARS-CoV期间CD4T细胞的耗尽与抗体产生的减少是一致的[66]。研究表明,在健康的年轻人接种流感疫苗后,Tfh细胞数量与流感特异性IgG和IgM抗体的产生相关[68]。尽管抗体滴度相对较短,但对SARS-CoV刺突糖蛋白的中和抗体反应也已被证明对易感宿主具有完全保护作用[69]。(5.4)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CD8+T细胞研究表明CD8+T细胞是病毒清除所必需的,过继将SARS冠状病毒激活的T细胞转移到SCID小鼠可提高存活率并降低肺病毒滴度[70]。因此,通过细胞免疫清除病毒感染细胞对于彻底解决感染非常重要。CD8T细胞与病毒感染细胞表达的Fas等死亡受体结合,释放穿孔素和颗粒酶,分别在细胞膜上形成孔洞和启动凋亡途径诱导细胞死亡来清除病毒感染的细胞。如果不加以控制,将对宿主组织造成灾难性的伤害。缺乏功能T和B细胞的RAG1(重组激活基因-1)基因敲除小鼠在大剂量接种流感病毒后延迟了发病率和死亡率[71]。此外,RAG1基因敲除小鼠中的病毒特异性CD8T细胞会加重肺损伤并加速死亡率[71]。6,上皮-内皮屏障损伤
如前所述,ARDS急性期呼吸衰竭的主要原因是发生气体交换的肺泡上皮-内皮屏障受损,导致肺泡腔充斥着含有纤维蛋白、红细胞和炎性细胞的蛋白性水肿液体,减少了肺泡气体交换,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9]。感染早期,甲型流感病毒通过直接抑制上皮性钠通道(ENaCs)而导致肺泡腔内液体积聚[13]。在感染的后期阶段,甲型流感病毒诱导的上皮细胞死亡是上皮-内皮屏障损伤的主要原因[14]。病毒感染的肺部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能分泌大量的细胞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IL-8/CXCL8、IP-10/CXCL10、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和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以应对病毒感染,并在感染期间将白细胞募集到肺内[9,72]。这些细胞因子招募和激活中性粒细胞、T细胞、单核细胞、NK细胞和DC,促进多种免疫反应,有利于控制病毒感染[67,73,74]。但是疾病的严重程度归因于甲型流感病毒复制的增强和促炎宿主细胞因子的高度诱导[75,76]。比如,IL-8水平升高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发病机制有关,ARDS可能是由中性粒细胞蛋白酶和活性氧(ROS)过度释放破坏内皮-上皮屏障的完整性,加剧了组织损伤[77]。IP-10/CXCL10还可能有助于白细胞的广泛募集,促进炎症反应和免疫介导的肺损伤[78,79]。CCL5/RANTES招募和激活大量的趋化因子可能会导致白细胞过度浸润和活性,从而损害呼吸道上皮。在感染期间,这些趋化因子水平的升高与更严重的肺部病理有关[77-80]。巨噬细胞可以通过三种方式破坏上皮-内皮屏障[9]。首先,它们可以表达TRAIL,TRAIL与上皮细胞上的死亡受体相互作用,诱导上皮细胞凋亡。其次,通过激活NOS,招募的巨噬细胞可以增加一氧化氮和过氧亚硝酸盐的浓度,从而导致组织损伤。第三,它们是促炎细胞因子的重要产生者,这会进一步加剧炎症反应,并可能破坏上皮-内皮屏障。7,机体的自愈能力
病毒很可怕,不加质控的话,引起的肺炎病理反应会很严重。但是,生命的神奇就在这里,身体有一定程度的自愈能力。病毒能诱导肺上皮细胞表达GM-CSF[81]。GM-CSF能刺激各种类型的免疫前体细胞增殖和分化。在肺部,GM-CSF诱导肺树突状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扩张和激活,这是有效的T细胞反应和病毒清除所必需的免疫反应[82,83]。缺乏GM-CSF信号的小鼠对呼吸道病毒感染高度敏感,而外源性GM-CSF是保护性的[83,84]。GM-CSF对上皮肺屏障有多种有益的作用,因为它保护肺泡上皮细胞免受氧化应激诱导的线粒体损伤[85],并在LPS攻击后促进Ⅱ型肺泡上皮细胞的增殖[75]。在Ⅱ型肺泡上皮细胞中高水平表达GM-CSF到局部高水平的小鼠可以强烈地免受感染和损伤[82,83,86,87]。通过吸入途径应用GM-CSF可能代表了一种有效的策略,可以促进肺宿主防御,改善肺炎相关性ARDS的氧合状况和预后[88]。单核细胞来源的肺泡巨噬细胞分泌肝细胞生长因子(HGF),一种有效的肺上皮细胞有丝分裂原[89-93],在IAV感染动物模型中诱导II型肺泡上皮细胞增殖[90,93,94]。组织驻留的肺泡巨噬细胞通过需要GM-CSF的途径促进内毒素诱导的肺损伤后Ⅱ型肺泡上皮细胞的再生,GM-CSF是肺上皮细胞的另一种增殖和抗凋亡因子[82,85,87]。8,总结及潜在的细胞治疗策略
如前所述,严重的病毒性肺炎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导致多器官衰竭和高死亡率[7,8]。ARDS急性期呼吸衰竭的主要原因是发生气体交换的肺泡上皮-内皮屏障受损,导致肺泡腔充斥着含有纤维蛋白、红细胞和炎性细胞的蛋白性水肿液体,减少了肺泡气体交换,并导致严重的呼吸衰竭[9]。研究表明宿主抗病毒防御系统的失调可能是呼吸道合胞病毒诱导的严重肺部炎症发生的基础[50]。因此,在病毒感染的早期,机体在肺部的免疫反应的出发点在于清除病毒。执行直接清除病毒功能的免疫细胞包括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NK细胞等。如果在这个阶段,及早输入具有具有杀伤病毒功能的NK细胞等细胞,是否能阻断病毒的持续复制?病毒不再持续复制,那么就可能不会引发过激的免疫反应而损伤自身肺部组织。病毒感染肺部后,最终会影响免疫细胞募集和促炎介质释放的程度,从而导致免疫病理性损伤的发生。肺内稳态的恢复发生在病原体清除成功之后,包括炎症消退和清除过度浸润的肺免疫细胞。但是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来稳定肺上皮-内皮屏障。虽然身体具有一定的自愈能力(人体中含有多种干祖细胞),能释放一些生长因子来修复损伤的肺组织,比如GM-CSF和HGF。但是如果患者自身没法提供足够多的生长因子来修复病毒和免疫反应所损伤的肺组织,那么患者将无法熬过呼吸衰竭这一关。当患者自身的间充质干细胞(MSC)不能发挥促进自愈修复的功能时,适当地补充健康足够数量的MSC将有利于肺部组织的修复,有利于促进上皮细胞和内皮细胞的修复和增殖。MSC发挥修复损伤的组织器官的治疗作用具有多靶点和多重机制[95],除了分泌一些小分子物质和细胞因子(包括GM-CSF和HGF)[96-],还在于减少炎症和减少组织细胞的凋亡[]、促进内源性组织器官的干祖细胞的增殖[,],从而达到修复组织器官的效果。同时,MSC的免疫抑制作用[-],将有利于减少病毒感染后期引发的过激免疫反应,从而减少了过激免疫反应导致的肺部组织的损伤。当然,由于炎症环境也会抑制了MSC发挥治疗作用,因此在重症肺炎阶段,不应该单独依赖MSC来发挥治疗作用,而且采用综合疗法。简而言之,综上所述,有科学假设如下:在病毒感染的早期,提高患者的免疫力有利于病毒的及时清除,而不至于因病毒大量复制引发的免疫过激反应而导致肺部的严重炎症损伤;在病毒感染的晚期,肺部组织破坏严重,而患者无法及时自我修复之时,可以适当补充健康的间充质干细胞,从而促进机体的自愈能力,使肺组织恢复正常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上述科学假设,即在病毒感染发展到免疫病理损伤过程中,哪个阶段适合哪种细胞治疗,只是一种理论假说,依然需要和值得去充分研究和探讨,尤其是介入时机的界定。相关文章:新希望:干细胞有望治疗“冠状病毒”引起的重症肺炎做好质控很重要:必须重视干细胞治疗的安全性长文分析MSC的功能特性和临床挑战快速让你掌握MSC的治疗机制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